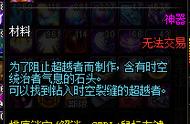关注 ,让诗歌点亮生活


《木雅藏地》 伦刚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诗人简介

伦刚,四川蒲江县人。曾于四川峨眉山、雅安、大邑、蒲江等地经营书店。2007年起幽居家中。2010年深入木雅人的故乡苦西绒,2013年十月底开始关于木雅藏地的诗歌写作。在《诗刊》《星星》《草堂》《四川文学》《诗歌月刊》《绿风》,台湾《海星》等发表诗歌。诗歌被选入多种诗集。诗集《木雅藏地》于2023年10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木雅藏地》诗选
木雅小男孩往长筒藏靴里藏土豆
小男孩把土豆一个一个
藏在他阿爸的两只长筒藏靴里——
丰饶之窖诞生了,无人能及
这不是宗教仪式
那两只靴子不再饥饿,他知道
他像老工匠一般熟练操作
他的拳头小过土豆,他二岁半
像个梦想家在土豆中制造光阴的可卡因
麻醉我
我蹲下,把一个土豆放入靴子里
小男孩把这个土豆捡出,放在地上
然后重新捡起放入——
他是自主神经的消防员
小男孩自在地埋头盈利——附带把我绑在土豆上
这土豆太烫,如果能与造它的手相遇多好
它是尧、舜、老子的土豆,我不能吃
这是小男孩正数的发明
亿万个土豆,只有靴子里的三十多个与众不同
它们不是野鹿关进动物园
它们是儿童的国度中充满童真的拥趸
那靴子好客,鼓囊囊的
小男孩抬头看了看我——贫病的成年人
决定与土豆召开紧急会议,拨款救助我
三粒松芽
前年还是去年遗落的松果?
腐烂,在阴暗潮湿处
我蹲下
松籽三粒出芽:
青绿神采,印证周遭清新空气
如三小孩出门迎客:
从翻卷的烂鳞甲缝探头……
我闭眼,即可在脑子勾勒成长的素描
若光线祝福——
三棵幼苗必有两棵死去一棵成活长大
根将穿透松果钻腐殖层深入泥土
生的循环在脚下起伏
驻扎苦西绒峡谷
我在此漫步已千年
活得像山神抗逆光阴
四周疯长的真菌、虫子出没于草木中
三粒松芽依附母体,自成宇宙
我盯视,俯身闻闻
坠入毁灭之神和生殖之神双重的气味
困在塑料桶里的豹猫
推开牛房门,高深的塑料桶里传来噼噗的响声
我蹑手蹑脚走过去:
招人喜爱的花斑小豹猫困在空桶里
它定是用后爪抓住塑料桶的边缘,失足坠入
它呜呜低吼,胆怯又凶狠的双眼死勾勾盯着我
我嘘它
它颈毛脊毛奓立,慌张地蹦跳
但用不上力,否定性地连续翻转
我戴上手套,试着伸手救它出来
它龇牙哭叫,以为死期到了
我如何告诉它:人并非全是陷阱?
当心,我把一根树枝放进桶里
实用性和熟悉感施行拯救之道——它瞬间抓住
蹿出来,消弭了困苦
树枝躺在地上,略带得胜之形
塑料桶,则显出虚空的原貌
喊 叫
我翻越木栅,跳进青稞地
小男孩在轰隆的溪流对岸向我挥手
用木雅话高声喊叫
我用汉话大声回应:
我没踩青稞,我看风景……
他继续喊叫
我想他是叫我去他家藏楼喝酥油茶吧
我用木雅话大声喊道:我不去……
你看青青的青稞在风中生起涟漪
像豹子奔跑时起伏的皮毛
我随波摇荡,陷入招魂的迷阵
小男孩继续焦急地喊叫,混合溪流的轰鸣
我摸不着头脑,朝他挥手
他捡石朝我投掷
我赶紧走出青稞地,翻越栅栏,跳下——
乱石草丛中,一只瘦弱的灰狼蹿出
一瘸一拐拖着折断的左后腿跑向灌木丛
我仍惧怕,转身翻越木栅,跳进青稞地
病痛的灰狼不知我欣赏青稞时的灵魂之美:
起伏的青稞有神灵居住
但他抛弃了灰狼——
生命的黑暗侵入它的四肢、身子,正在毁灭它
狼毒草
狼毒草有沸腾的毒汁
做印经纸
连时间都怕
更不必说老鼠、蛀虫……
狼毒纸上的经文一千年后仍对你呼吸
令刻经的木头、石头心生忌妒
它不像贵妇打扮
它不说奉承话。它的缺陷是:
顽韧是它不可救药的自度
它还是草时,就已是超级*手
其内在的哲学,无法被驳倒
它前进
没有人说它是坏蛋
但牛马遇到它时,嘴立即绕开
它有冷酷的定理,别靠近它
从未听说过它的毒性发作
毒是它的自性
吸毒者无法模仿
印经人用它造纸
每道工序都为它招魂
它成了纸的楷模
浩瀚的《甘珠尔》《丹珠尔》
爬上去,不可抗拒——
靠有毒的纸救助
反过来,《佛经》赦免了狼毒纸的毒——
纸在之处经在
恶在之处佛在
(狼毒草,是藏地高原上一种有剧毒的草,用于造纸;所造之纸被称为狼毒纸,是印经的绝佳材料,千年不坏。藏文《大藏经》浩瀚、深邃,被纳入两部总集《甘珠尔》和《丹珠尔》中。《甘珠尔》即《佛经》,《丹珠尔》是历代高僧大德的注释和说明。)
投 宿
我从悬崖小道下行时
曲梅巴珍手握镰刀,站在一块悬空的巨石上
拖腔拖调喊“扎西—德—勒—”
我回头对她喊“扎西—德—勒—”
喊声像神性的交响乐把峡谷震荡——
这歌剧的野性台词从寂静中来
暮色从谷底升起
他们从悬崖边割了一半的夕光照亮的青稞地下来
背着青稞啊啊呀呀说着木雅话
我等着
之前,我在山顶投石决定住在谷底三座藏楼的一座
当曲梅巴珍叫我时,我感念因果
决定住在她家
而她家就是我投石决定的那家吗?
她叫我就是今世的精神关照
她擦着脸上的汗水,我夹在她的亲人中
心情夯实了
风绷紧黑暗的峡谷迎接我
走进藏楼——
正是我投石的那家
喝着滚烫的酥油茶,我内心喜悦
这忘却的夜,仿佛我从隔世回来
在来去中重新投胎
躺在雕花的藏床上想起曲梅巴珍走路带动的裙角
她擦去皱纹里的汗水,笑着……
我在黑暗里也轻轻笑着——
在她的喊声里,我是抬头回应她的亲人
日照金山
我爬上危崖巨石时,夕光中的惹哈厄洛——
雪豹的城堡,堂堂流金
与我迎面相撞——
脚踵为神界金光灿灿的化境一个趔趄
我何以站立不稳
目醉神驰了——
那荒古野马,那烽燧般的祭祀,那野火的抽搐
使我丢掉刹绳
急如天鹏排卵,飞掠危崖而去
又如泥雕傀儡摇撼
与当当洪钟击撞相呼
东天那轮弯月,怦怦心跳而至
恪守荒原,羊脂玉那般娇媚
我心中的一滴蜜笑了
仿佛播挂在惹哈厄洛雪峰尖上的诗句
滴下不可塑的红色的甜胎液
仿佛炼丹大仙拴马柱上的骏马儿已然断缰释放
簸扬金色的炼火
我感动了:
为金山上的一只一只兽崽掰开小眼
痴痴地,咕叽咕叽
蘑 菇
一朵红蘑菇,宛如折光的红宝石,跃出黑土;
又一朵,蓝如翡翠,抿了抿酒窝;
再一朵,渐次入林,如处子偷觑,跺了跺脚;
还有一朵,区别于浮躁的鸟儿,
眨了眨睫毛,意趣融融,彬彬有礼……
我猜想:它们是上帝的访友,
但不喜欢天堂,
佩着自家的圆顶草帽,一路追赶,走下天梯,
如苍穹星宿,停在林野的厩棚,依依,
特许我们的手指信守誓约——
摘取,如弥撒仪式;古雅,似圣礼席卷。
喂红头穗鹛
在牛房后用黑青稞粒喂红头穗鹛
为使它走近,我边喂边退
不经意碰倒了靠着树*木棍
彩鸟儿吓得不轻,转身飞上大树下的柴垛
奇怪地尖声大笑咳嗽,用尖喙梳肚子红绿色的羽毛
为证明我是大买主——能挽回损失
得到彩鸟儿奇异的香料,我一再后退
欲与它签个无限庄严的合同:
打开造物主的口袋,借这长羽毛的偶像
穷追内心的真金,说彩鸟儿是惊人的女孩
可升格为母亲,饮饱后成为万物之门
看我退远靠着巨树,彩鸟儿冷静
飞落于黑青稞粒撒落处,像福气长出百张嘴喙
游戏般快速啄食,滴溜溜的绣眼在我的双筒观鸟镜里
天恩般飞瞟……压根儿我不存在
填饱肚子后,彩鸟儿飞上枝头有滋有味地一声嘀呖
像吹了个陈述的气泡——出神入化的一笔
穿越恭敬的荒林,古怪地暗示
仿佛纳罕助我一臂之力:挑逗我灵性的耳鼓
然后吹着四声哨音,飘拂彩色的衣裙飞走
这超越生死的居民踩着独轮把天堂铺陈
仿佛千业百行已讲明自身的目标——
开了榫眼——我垂手抓住观鸟镜像挨了蜇:
灵魂的神经元滴落寂静
跛腿马
一大早,跛腿马用嘴推开牛房的木门
把积雪的头伸进来——
我躺在火塘边的睡袋里暗自欢喜
佛祖也一定欢喜
“坦布——,坦布——”
早起的圣徒泽仁德吉用木雅话向它打招呼
拿个加盐的糌粑食团喂它
它抖掉头上的积雪,鞠躬敬礼
“跛腿马,跛腿马……”
小孩们有时围着它欢叫,戏弄它
甚至伸腿想把它绊倒……
它不计较,踩着自己的影子
悠闲地扇耳甩尾吃着草——
它知道自己本是跛腿马
它不能驮物驮人,也不能挤马奶
没办法地一年一年地衰老
但主人从不打它骂它,也不卖它
它本是他家里不可或缺的一员——
这,它知道
绿度母也知道
外面的雪呀,哗啦哗啦
烧着火堆的牛房木屋暖和舒服得像宫殿
跛腿马推开门把头伸进来抖落雪——
我的心怦怦跳:
跛腿马,跛腿马
你不是客人,而是主人
(坦布:木雅话,早上好。用于中午之前的问候。牛房:牧人放牛牧马时,可煮饭睡觉的木房)
藏区农耕图
缓缓倾斜的留着禾茬的青稞地
两头公牦牛步幅一致拖着犁铧,按坡地弯曲的走势
耕犁一条条土的波浪
为何丹增达吉透亮的口哨在银河系
耕出我心魂的线条,涌出铜色的气流
混杂的各种雀鸟从山林唧唧喳喳飞进地里
像活的浮标,急不可耐地飞跳在耕者身后啄食翻出的虫子
使我古旧的心也随之作分子运动
并像藏区农技员看着松软黝黑的泥土,盼着下雪
两头大汗淋漓的牦牛毫不刻意地拉着犁铧来来回回
轻松悠然地绕过地中巨石,极富活力
丹增达吉是个高个子,头戴藏红色圆盘毡帽
他耕犁的喝喊回荡河谷,打开我的多重想象
地边的火堆煮着大茶,映红他的妻子益西巴姆的脸庞
风偏了方向,一会儿又紧逼火焰从另一个方向过来……
我看清了:这高原藏地的千年农耕图
使我难以逃遁,可雕刻心灵的铜版
上达度母的福祉,且有不可描述的心象铜绿
星月之光
我喜欢所有的光,有一种光是冷的
那是黑夜匠人制造的星光晚宴
它那么远,像记忆深邃而遥不可及
像心灵渴望的美和高度
许多个月夜,我沐着月光走进荒野
攀上深渊之上悬空的绝壁顶
眺望浩瀚无垠的天穹星月辉映——
人世万物在眼前消失了
我见过火月亮
就挂在原始森林牛房西边的上方
移向野牦牛翻越的荒凉险峻的垭口上空
巨大无比,金红,高悬苍穹
诗意饱酣,像老友突至的拜访
难以忘怀,难以置信
辉映我心灵的孤独和苍茫的憧憬
有一次,我们夜间沿山脉徒步西行
马儿打着响鼻,牦牛哗哗踩响石子
驮着盐、酥油、糌粑、大饼、奶饼、奶渣……
为无人区荒野采虫草的木雅人补充供给
我们跟在牲口的臀尾,赶着它们
连绵的雪山冰峰在星空下更加庞大阴森
始终在我们的左侧,随我们一路西行
火月亮出现了,在雪峰之巅硕大金黄
那一刻,我心魂抽搐震颤
仿佛置身于太古之初的寒疆荒漠
伸手就可碰到高天的月亮
而黑暗的深渊激流就在脚下恐怖地
砰訇怒吼

序 言
精神家园的范式
赵四
为伦刚诗集作序似乎是我责无旁贷的义务,因为我几乎可以说是看着他的《木雅藏地》在十年光阴中如何一点一点长成的。
每年,伦刚总会选择一段特定的时间,生活在川西木雅人中间,生活在木雅人生活的那片神奇、原生高古、莽苍荒寒的雪域藏地。木雅人,这个十几亿中国人中可能没有多少人听说过的藏族人已是汉人伦刚此生的亲人们;格桑曲珠、扎西旺姆们,已是他精神骨血中的弟弟、妹妹……
来到大荒之地的诗人伦刚是有福的,他满眼皆诗,荒古之诗。这本是他心灵先天的位置,他的心灵原就为这样的景观所充满,原就是从这样的自然中生就、长出的;只是长久以来被城市生活的烟幕所遮,以至于他自己已不知其家何在,以致他初睹这熟悉的陌生之地,身心五味杂陈,惊惧、惶恐、狂喜、震慑、悲欣交加,也即全身心被诗充满。
多年来,他一直不停地出走城市,走进内心,走进他内心本原里的荒古,走进他的家,他原本与万类同在的家。他只需一座牛房木屋、一方火塘、一盏酥油灯、一首木雅古歌、一个青稞大饼、一碗酥油茶、糌粑、奶饼、奶渣……即可安顿此身;他原本就是劳动、采摘、听鸟、观星、歌舞、通灵、娱神娱己的构造;他的虚构、抒情天赋原就不是为占有、攻取、统治、服务于他本无需的种种身外之物而设。
在川西木雅人的故乡雪域高原大地上,伦刚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他无上感动、生出作为诗人的自己。他在这里参诗、参佛、体悟万类;他恢复他原本所是,在这里背石修藏楼佛塔,种青稞收青稞,挖虫草,采松茸,放牧,参加庙会,参加木雅婚礼,孤身游荡,与牦牛、马匹、林麝、马麝、岩羊、红狐、熊、狼、雪豹为友,眺望蜀山之王贡嘎山和惹哈厄洛神山雪峰、仰望燦燦星空,让内心里的苦寒孤寂在飞雪、冻土中一望无际,让灵魂中的童真奇趣在耳中鸣啭、嬉游目遇中珠玑闪烁,他凭此将自己成就为本质意义上的诗人——那个自然怀中的原初精神体(如果我们仍同意人为万物灵长的话)。
这里正是精神家园的原初意义之所。精神不是凭空而在的,东方信仰也并不能悉心认可一个完满普纽玛的万千流溢,它宁可眼见为实,它最坚实的基础就是看得见的自然、荒古及其在在万神;而精神的更生也从来没有不经肉体的重置、颠覆(尤经劳作困顿)就能完成。现在,这位诗人来到这里,踽踽独行,重历他的万古往生,重生他的肉身之人为诗性的人之存在。他因而占据了一个比如今绝大多数诗人(被文明驯化或蓄意反抗驯化的分行写作者们)都居先而在的位置,一个真正受赐福的本原诗人之位。
而在地方性的文化意义上,这位诗人又完全开发了一部旁敲侧击的木雅人精神史,以他一个异族归家者的个体精神史折射出了木雅人生息大地之精神存在的丰富可能性。正是归家者在离家之时获取的所有文化储备返乡时与家之本原万类遇合所具有的内在张力赋予了这种精神存在以文化意义。木雅人本有的精神存在之内涵无疑更多地体现在他们自己的信仰、古歌、舞蹈、工艺、艺术形式中;只是往古以来,到了此刻,在《木雅藏地》里,木雅人大地才终于获得了自己在汉语中的诗性存在,并因其广阔的文化观照、对参,而获得了一种新的具现代性的文化身份。伦刚无疑是为他们带来这种文化身份的使者,是他们的诗歌大使。伦刚个人的福祉亦是木雅人的福报。
一首《巨石上静坐的火狐》,便是一阕完美证词。
火狐在黄昏独自上演沉默的歌剧——
没有舞蹈,没有歌唱
蓬松的火尾抱在怀里,在风中炸开
像管弦乐队无声演奏
它蹲坐的巨石是古老的剧场
荒野:背景
乱石:听众
红毛:戏服
宁静露出它骨子里的戏剧性
荒风削删掉红色演员的身外物
一场时间救赎的歌剧
大寂静里有一切歌的起源
红色演员对话雪山、黑石
时光张望着它
我以舌的缺席、耳的在场拎起全副身心
听懂了它领唱的大荒咏叹调
一只火狐,便是一出自然生灵的戏剧、一场寂静的奇异歌剧;它不发一言,只是静坐荒风中的巨石剧场,便领唱了一部天籁的大荒咏叹调。歌剧、剧场、咏叹调这些现代生活、艺术形式内容联想,无疑远离木雅人的生活,但在这里,它们不仅不暌隔于荒野大地,反而赋予了它奇趣、深度,使其显现出不可思议的融会之魅力。这便是广阔的汉语文化内涵穿透一位优秀诗人而赋予古老大地以新的精神、文化意义之法,是唯高明的抒情诗所具有的万古未离的神巫之力才能给予大地的馈赠。
通过这样的一首诗,我们也能够体会到,伦刚的诗歌写作无疑是极具现代性的,无论是在诗人的诗歌意志还是文本的诗歌技巧、语言创造性方面。红狐并非象征,凭着诗人言之力呈现出的兀自存在感而完成为心魂中的造像,由自然之物提升为言铸的心像,而非诗人主观的心想,这个诗人断乎是个现代的创造者-艺术家无疑了。
伦刚是个心怀热爱的沉郁、质朴的诗人,他扬其具长歌浩荡之气的诗风,在精神更生的寒疆荒野里,观察、聆听,获得知识,心怀敬畏,时时体会心魂的悸动、震颤,以呕心沥血的一字一句创生出一个介于神人之间的消泯了时间的永世生灵。精神化作章章诗篇,完成自己宿命的大地诗性行旅。
这位诗人置自己于荒古冰川下、放牧的荒野无人区、采虫草的高寒极地、采松茸的原始森林、木雅婚礼现场、风马旗林、泥擦擦屋前、佛庙之中,塑一帧帧荒野生灵的造像,绘一幅幅木雅人生息的图景……更重要的,这通灵的古老诗人更是以万类为自己的精神寓所,不时地,他自己便是牦牛,便是马,便是藏地儿童、放牧老人、林神、水鹿、熊、悲鸣的夜鸟,是危崖孤峰、淙淙溪流、涟漪起伏的青稞、恐怖的暴风雪……在到处是野兽的崇山峻岭中,人也仍有幸还是无染的“人兽”,只是这一个,诗人,他来自文明世界,携着语言的致胜武器,以阅读种种诗歌大师之作奠定的内在文学准心捕猎着他的大地之诗。因为在这人的领地可以轻易被自然大荒消融甚或抹去的所在,他,一个诗人若不来此,便无以赎出人对万类的分享和敬慕、悲悯与超度,人便只是此地的人-花自开自谢,人-兽自生自灭。
一直以来,伦刚都从不放松以最大力量和最深厚可能性把自己投入进诗歌,在文本生成的过程中深探自我和万类、和神性的关系,有时甚至不惜以“过度表达”为代价,尤其在信仰直接于心灵中占了上风的时候。但他往往是在那些放松的、甚至不乏孩子气视角和语调的诗篇中,有着出人意表的超常发挥,在一些大巧若拙的杰作中,他甚至写出了神力加身的完美童话,让人羡慕。“松弛”的状态对诗人向不友好,极少以之对真正的诗人青眼相加,但对通常紧张度偏高的诗人如伦刚,“松弛”却不时对他伸出慷慨援助之手。这或许也是每一个好诗人天生的机智、狡黠总有藏不住自己,在端庄的理想背后偷露一小手的时候。此时,其实是一个严肃诗人被赐福的时刻,是某种福佑力量左右着他的笔而使他写得最为自然的时刻。好诗,总常常是各式各样的意外:语言的意外,想象力的意外,思想力的意外。
像他的《木雅小男孩往长筒藏靴里藏土豆》《月亮》《蘑菇》《扑笃,扑笃》《偷酥油的小松鼠》等都给予了我极为欢畅愉悦的阅读体验;《水槽里的月亮》《喊叫》《三粒松芽》《无法命名的*死獐子的小动物》《荒野(昨天,我把荒野背进迷梦)》《积雪的原始森林》《老树倒下》《森林夜,暴风雪》《左前腿骨折的马》《喝水的马影》《关于诗人工作的性质》等等诸多诗篇,也常常让我赞叹不已,品之再三。
篇幅所限,这里仅和大家一起欣赏一首小诗《月亮》。被简直可称为“月亮部族”的古往今来的诗人们仰望、想象、抒情了无数遍的这一地球上空永远的白玉盘,面对它,你我还能有这样簇新的、与神同在的发明能力吗?
月亮病好了后,面色红润
身上涂了黄油
巨足从雪峰顶一步跨入破碎的云朵里
那里是它的缮写室,长庚星是它的耳堂
我依着牛栏,影子倒向圈里
同牦牛一道卧伏
牛房后林中夜鸟撒了一撮光阴的灰烬窃笑
我微眯眼,清冷地接着月亮飘下的一片光羽
感到被无我重新雇用——
在生死的路途
月亮是月亮的庙堂,我是我的
若要对伦刚再有什么寄望,我只想提醒这位已然荦然自成的诗人,“无目的的目的性”之游戏精神从来是文学创造的不二法门。如何在文学创造与精神性表达之间,最大程度地享用“松弛”领地,取得最佳的完美平衡,仍然是伦刚需要持续修习的功课。
赵四,诗人、翻译家、学者、编辑。在《诗刊》供职,同时任《当代国际诗坛》副主编,任欧洲荷马诗歌奖副主席,主编“荷马奖章桂冠诗人译丛”。在海内外出版有十余种著作,包括诗集《白乌鸦》《消失,记忆》,小品文集《拣沙者》,译诗集萨拉蒙大型诗选两种《蓝光枕之塔》《太阳沸腾的众口》,霍朗《与哈姆雷特之夜》,特德·休斯《乌鸦》《季节之歌》《利尔本诗选》等,《门槛·沙:雅贝斯诗全集》(合译)。
福利赠书

《木雅藏地》在当当、京东、淘宝、天猫、抖音等平台有售
留言分享你对伦刚诗歌的阅读感受
我们将从留言中
挑选 3 位读者赠书
截止时间: 11月15日 周三中午12:00

双十一
特价订阅2024全年《诗刊》!

识别二维码,订阅2024年《诗刊》
编辑:王傲霏,二审:曼曼,终审:金石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