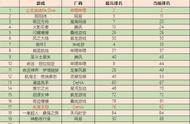小拇指粗的钢筋拧成一条一米多长的鞭子,抽打在屁股的同一个位置。童婕被三四个女校的同学摁在床板上,她挣脱不开这几张朝夕相处的脸。为了确认学生没有在臀部垫东西逃避责罚,男性教官甚至会直接用手“确认”。剧烈的耻辱和疼痛将童婕淹没,她几乎麻木地在心里倒数着惩罚次数。“千万不能想家,一旦想家就会崩溃”。在豫章书院的两年里,她一直这样提醒自己。
然而,家,对童婕来说是一个悬浮而依托于想象的概念。因为不够“温顺听话”,她被父母从河南郑州的老家骗去江西的豫章书院。2017年,豫章书院被曝光对学生实施严重体罚、非法拘禁等,童婕特地跑到江西亲眼见着它的大门彻底关闭。然而和豫章书院类似的学校依然在暗处滋长。
2023年3月31日,豫章书院案在江西萍乡市安源区法院开庭重审。但更早之前就出现在书院学员家庭里的裂缝并未因此弥合。从豫章书院被曝光到案件进入重审的六年里,隐藏在正常生活之下的噩梦、应激反应和精神疾病仍会时不时将他们拽入年少时的沼泽中。他们不知道是否应该寻求一个解释,向谁寻求解释。
如果说家是牵住孩子的风筝线,当年的学员们并没有感觉到温柔的牵引,那根风筝线或是在激烈的拉扯中愈绷愈紧,或是在沉默的游移中越飘越远。
完全没有人管的伤口
2014年10月的一个秋日里,14岁的周禹诚和几个社会青年朋友正从网吧出来在街头闲逛,他脑海里还回荡着穿越火线里机枪突突突的声音。他厌恶学校,但对暴力和冲突感到新鲜,一旦和人发生口角,他和朋友们会毫不犹豫地拿拳头砸上去。
脑海里机枪的声音还未停歇,一辆面包车停在了他面前,车上跳下来几个自称是警察的男子,他们喊出了周禹诚的名字,拿出一本类似档案册的东西走到他面前,要求周禹诚和他们走一趟。脑袋还在发懵中,他已经被拖上了面包车,随后被搜走了身上包括手机在内所有的东西。七八个小时后,他从浙江湖州被送到江西南昌。
23岁的彭月月仍然记得9年前的那个4月,她被母亲用旅游的名义骗上飞机,一落地就被教官们接到了豫章书院。她看着母亲的身影在大门外渐渐远去,压抑的不安涌上心头,她拼命奔跑着想追上母亲,却被教官抓住,挣扎换来的是几个教官扯住她的头发,把她按在地上,那是她“这辈子最屈辱的时刻”。

家长与学院签订的入学合同
然而这仅仅是开始。彭月月随后被强行脱掉上衣,关进被称为“烦闷室”的小黑屋。里面阴森潮湿,爬满蚊虫,因为连着厕所,臭气熏天。她试图用绝食的方式进行反抗,三天后学校的主任找到她,表示不怕她饿死,随时都能给她打营养针。
“到处都是铁丝铁网,像个牢笼。”周禹诚和烦闷室里的另外两个新生制服了监督他们的教官后试图逃跑,却被巡逻的教官发现,打了他三“龙鞭”,那是一种用钢筋做成的拇指粗的鞭子,打在身上火辣辣的刺痛。“三个以下的龙鞭不用通知家长,三个以上的,他们会告诉家长,你小孩犯了什么错误,我们要略施惩戒,一般十个起的比较多。”
没有人敢在被老师全程监控的电话里哭诉或是讲方言,在豫章书院困了两年的童婕明白,一旦有人尝试在家园游学会的开放日上和父母诉苦,大门一关,所有学生都要受罚。即使后来父亲知道了周禹诚在豫章书院里的遭遇,他的反应也只是一句“不乖就是该打”,只不过对儿子的施罚者从他变成了第三者而已。
在看不到尽头的日子里,各种各样的体罚成了他们的共同记忆。周禹诚因为偷偷抽烟被教官抓住,打了十个龙鞭,他的臀部全是青紫的淤血,一周里都要趴着睡觉才能缓解疼痛。“完全没有人管伤口,但比起那些本身有精神疾病的学生,我算幸运了。”
彭月月记得,自己被打得最严重的一次是因为在上课的时候翘了二郎腿,被记录员记名,原本的惩罚是五个戒尺。“戒尺很锋利,也很重,打完基本手都发黑了”。因为她疼得不敢伸手,教官让她去一边等着。等到所有学生挨完惩罚归队后,彭月月被单独带到没有摄像头的办公室里,被四个男教官和两个女老师抓着头发按在地上殴打。
“日复一日,除了挨打还是挨打。”在身体的疼痛之外,还有精神上的侮辱和贬低,以及由告密和连坐制度产生的怀疑和隔阂。
轮到彭月月负责厕所卫生打扫的时候,教官不提供疏通工具,她只能用手一点点把下水道口的秽物清理干净,此后的十几年里,她只要一闻到这种潮湿腐臭的味道就会无法自抑地喘不上气、开始干呕。
童婕亲眼见过同学的崩溃。在这座以国学教育作为宣传点的书院里,女生会遭到更苛刻的对待。因为在队列里整理散掉的头发,一位女同学被女校校长吴淑媛冠上了勾引男生的罪名,并拿男生们穿过的袜子串在一起,要求女同学随时随地戴在脖子上示众,吃饭也不能摘下来,不然就会挨打。晚上在大通铺睡觉的时候,童婕总能听到有细细碎碎的哭声,“数不清,都在偷偷地哭,不敢哭得太大声。”

豫章书院的女校学员
我是个怎样的孩子?
为什么父母要把我骗到或是抓到豫章书院?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学员们心里有着相似的愤怒和怨恨。然而在一天天的挨打和煎熬里,最初的不可原谅似乎越来越动摇,父母成了他们最后的支撑和依靠,这是作为孩子无法控制的本能。
在豫章书院的第二个月,彭月月在日记的末尾写下:妈妈,真的好想你呀,你过得怎么样了?!妈咪都不来看我(沮丧脸)好想妈咪呀(哭脸)。那或许是她对母亲情感流露最真切也最复杂的时刻。此前,在母亲质问她为什么不喜欢上课,或者用衣架直接抽她的时候,彭月月从来都是沉默着不回应,这往往会让母亲更加生气。

豫章书院中学员的日记
彭月月出生在一个潮汕家庭里。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家里有姐姐和弟弟妹妹,母亲是家庭主妇。彭月月出生后,母亲出现了产后大出血,没有余力照顾她。她流转在各个亲戚家里长大的,直到小学才被父母接回家中,然而当时的她并没有明显的开心,只是不知道要说什么、要怎么和陌生的至亲相处。
“我不喜欢读书,脑袋笨,读不进去,老师挺好的,但就是不喜欢学校里的环境。”上初中之后,彭月月开始逃课,在学校里找个地方躲起来玩手机。尽管当时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很好,母亲还是省下钱来给她报了舞蹈班和书法班。
“四个孩子里,父母最喜欢的是弟弟。别的都比较乖,我可能是最叛逆的。虽然弟弟也不喜欢学习,而且因为打游戏休学了一年,但妈妈不会打他。”彭月月说不清楚,当时的自己是不是想通过逃学来引起妈妈的注意,她只是沉默着,也不为自己争辩。
3月27日对童婕来说是个禁忌,这是她进入豫章书院的日子,也是她在一年后从白天等到黑夜,也没等来父母接她回家的日子。“身边的同学都以为我能走了,但他们没来,好像忘了这事。”
“不温顺、不服管教、特立独行”是父亲对童婕的评价。在父亲看来,豫章书院不仅能管一些不听话的孩子,还可以教国学知识,符合他“棍棒底下出孝子”的理念。但童婕认为,这不是正常父亲对孩子的教育,“他对我的态度完全取决于他的心情,说白了是发泄”。她觉得父亲对她像是条养的狗,听话服帖就给点零花钱作为奖赏,顶嘴反抗则动辄打骂。但她不是宠物,一个具体的人怎么能被驯化?
29岁的童婕始终有个解不开的心结:初二的某个周五,她在晚自习后回到家里,询问父亲能否把自己送到姥姥家去看看老人。因为父亲的家庭暴力,当时童婕的父母已经分床而居,父亲和姥姥、姥爷的关系也并不融洽。
“我爸先是薅住我的头发把我从里屋拽出来,然后把我的头摁在床上,开始用拳头捶我的脸,又把我拉到客厅,我妈各种拦根本拦不住”,童婕苦笑着问:“你知道人的嘴唇是会爆开的吗?我当时眼睛里全是淤血,脸肿得不像个人,我之后一直反反复复地想这个事情,但我没法给他找到任何理由。”她至今记得当天的所有细节。
暴力对周禹诚来说也并不陌生。他觉得自己并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受害者,在豫章书院的大半年似乎没给他留下心理创伤。因为沉迷游戏,父亲曾经当面砸过他的电脑,用不堪入耳的脏话骂过他,打过他,甚至迁怒于母亲,认为是母亲的宠爱导致了一切问题。然而越是这样,周禹诚越叛逆,他在街头和人打架斗殴,整宿整宿地不回家。“他们知道跟我说了我也不会去(豫章书院),所以干脆直接让人把我抓过去了。”
周禹诚的姐姐成绩优异,因为觉得父母更偏爱弟弟,她在高中就选择出国读书,离开原生家庭。周禹诚却觉得自己和父母的关系比较疏远,“没什么好讲的”,自己和姐姐之间的落差更是让父亲的期待落空。他不明白忙于处理公司事务、没有时间管他的父亲为什么这么愤怒,就像他也无法解释当时的自己为什么在叛逆的道路上越走越偏。“软的不吃,硬的也不吃,就是个刺头,如果这是我自己的孩子,好像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的语气有些迷茫。
漫长的漂泊
从豫章书院被曝光到案件进入重审的六年里,这些父母眼中“不合格”的孩子也渐渐地踏入了工作岗位。童婕和周禹诚的父母没有关注过这所学校的后续,他们也默认般地将这段记忆埋藏了起来。“肯定恨过,但现在怪他们又能怎么样呢?到底是父母。”
然而当童婕在22岁时来到江西鹰潭,混杂着香火气的潮湿气味将她再度拉回了在豫章书院的时刻。“不管在这里经历了什么,都足以影响我们的一生”,她悲哀地发现了这一点。
作为最初原告之一的彭月月则在向父母要当时的合同和证据时听到他们的谈论:“这个学校现在被抓了”、“垃圾学校都是骗人的,真不是人!”但父母没在她面前再提起过豫章书院,她觉得心里有点难受,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缺一个道歉。
从豫章书院回家后,彭月月先是休学了一段时间。她频繁地做噩梦,梦里自己又被抓起来殴打。她并没有寻求父母的帮助,只告诉了身边亲近的朋友。“和爸妈一直话题很少,也学不会倾诉,我一度以为自己情绪感知不到位,直到和朋友讲起来,才发现自己(对父母)还是有责怪的。”
彭月月知道,父母希望她能安安稳稳地走在既定轨道上度过这一生。她不知道哪条是正确的轨道,但她不想像母亲一样做个家庭主妇,疲惫和憔悴鲜明地写在脸上。
初中毕业后,彭月月选择到河南的武术学校训练,一年和家里人就见上一次,疏离的沉默或客套的问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工作之后,她和家人们一起住在深圳。“在我这年纪,尊敬他们、孝顺他们是该做的,也是履行子女的义务,但他们不会是倾诉对象。”
把周禹诚从豫章书院接回来之后,父母像是彻底放弃了他。“我说不用再把我送去了,反正把我送去了也不会改的。”他整日辗转在网吧和酒吧之间,直到成年后父亲要求他去已经安排好的公司里上班,而他发现既没有学历也没有能力的自己只能接受这样的掌控。
“没读书挺后悔的,那时候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可能一辈子就这样了。”父亲对周禹诚的呵斥责骂从学习转移到了工作上,常常伴随着父子之间长达几天的冷战。有时候母亲会在一边默默地叹气,“你从小就这么不乖,让我这么辛苦”。他想起小时候倘若母亲不给自己去网吧的零花钱,他就会狠狠地和母亲吵上一架。但母亲如果给了,又要承受父亲的怒火和叱责。
在接受潮新闻记者采访的前几天,父亲刚把童婕从电话和微信的黑名单里放出来。“都忘记拉黑我多少年了,反正我在家根本待不了,过年也是在姥姥家过的。”童婕甚至不记得弟弟多大了,只记得偶尔几次碰面小朋友都很开心,和她的童年好像截然不同。
大学毕业之后,童婕没有像父母期待的那样找个本地的安稳工作,而是向他们借了一笔钱去广州创业。她起早贪黑地赚钱,始终觉得自己无依无靠、没有安全感,“总得有点东西让我寄托,人总得有点信仰才能支撑你活下去”。她想自己或许生来亲缘淡薄,然而最终还是选择回到了河南独居,并选择了皈依道教。
“其实我挺恋家的,但恋的不是自己的家,只是家乡这个地方”,童婕坦言。曾经有记者问过为什么经济独立了但没有选择逃离,她反问,难道经济独立就能和原生家庭割裂吗?
去年,童婕被确诊为躁郁症。每一天的日子就像开盲盒一样,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她形容躁狂发作时的自己就像疯狗一样。“医生说这个病有挺大的遗传因素,然后我情绪又压抑得太久,就像一杯水,慢慢地就往外溢出来了。”她试探着询问父亲有没有听说过这种疾病,得到的回应却是骤然的翻脸和指责:“我们家哪有精神病,就是你自己作的。”
“豫章书院”并没有消失,打着“行为矫正”、“戒网瘾”等旗号的素质教育学校仍然层出不穷。17岁的小俞去年刚从湖南的一所“法制教育基地”离开,她一直在等着自己成年的那天。“我现在还要念书,不念书我早跑了。对我妈妈没什么好恨的,我就想逃离,逃离这个原生家庭。”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童婕、周禹诚、彭月月、小俞为化名)
“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