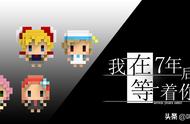性别不仅与战争有关,而且是战争的核心。在沉重的压迫中,女权主义者的战争体验超越了单纯的被动受害者——女性可以为平等与和平而战。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世界大战还是地缘冲突,战争都很少以女性的经历作为理解政治矛盾、权力冲突甚至颠覆统治的出发点、视角和心理基础。战争的发生、呈现和叙述往往充满了男性气概,这一切都源于男性记忆,围绕着男性的羞耻或希望展开。在战争的政治话语中,女性是天真和被动的对象;妇女是无辜的,是受战争影响的寻求庇护的难民;女人是点缀,是衬托战争惨烈和男人英雄主义的道具。1940年8月28日,英国诺福克郡凯特林厅的凯特林厅训练中心,急救护理志愿者(皇家公主志愿队)成员正在进行一次演习。

1940年8月28日,英国诺福克郡凯特林厅的凯特林厅训练中心,急救护理志愿者(皇家公主志愿队)成员正在进行一次演习。
然而,“男人制造战争,女人承担后果”的简单叙述片面地简化了性别与战争的关系。从安史之乱的杨贵妃到神话中的海伦,男人都是用女人的借口来发动战争。从孟姜女到花木兰,女性可以是战争的动员支持者,战争的直接参与者,甚至是反对战争的动力。另一方面,国际争端和民族冲突似乎总是排斥女性,将她们视为不重要的边缘群体;但无论是保家卫国,支援救援,还是提供支援,战争其实都需要女性。战争通过性别化的民族主义叙事来神化女性。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的权力运作极度排斥和贬低女性,不把女性当作真正的行动者。女性在战争中的经历往往被剥夺,战争史中关于女性的记载仍然存在真空, 而女人成为战争的丑态。
如果说流离失所、沦为难民、被性侵、沦为人贩子的猎物、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是战争对女性造成的直接伤害,那么战争对生活方式和社会稳定的影响、对包括自然环境在内的可持续发展的威胁、对公平正义的剥夺则构成了结构性暴力——战争不仅是一个硝烟弥漫的地方,更是终极暴力,是摧毁意志、强加暴力的权力关系。本文聚焦地缘政治冲突中的女性,探讨战争暴力和战争下的性别化国家叙事,通过回顾战争中女性行动者的处境和经历,重申女权主义和平运动和反战的和平主张。

女人的身体是另一个战场。
历史上,战争和性暴力是相伴而生的孪生怪胎。女人的身体是战场的一部分。慰安妇、军妓、战争性侵等不堪忍受的现象成为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角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军事入侵和伴随的强奸是普遍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臭名昭著的日军慰安妇制度是国家会在军队管理制度中有系统地利用对女性的性犯罪来达到战争目的,这使得中国、菲律宾和朝鲜半岛的大量女性遭受非人待遇。
二战结束后,虽然全世界迎来了基本和平的历史阶段,但在地缘政治冲突中,女性一直是战争的牺牲品。1991年前南斯拉夫内战中,“种族清洗”成为大规模强奸的借口。1994年,胡图族男子在卢旺达冲突中强奸图西族妇女,导致著名的“战争*”;1998年印尼政治剧变期间,印尼华人妇女遭到集体或公开强奸。据非政府组织估计,至少发生了168起强奸案,甚至有1200名中国妇女死亡。
面对这些惨痛的历史,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
战争性侵的发生,不仅仅是因为军纪不严,个别士兵性欲强烈。学者韩冷总结说,强奸与其说是为了性满足,不如说是为了满足对弱者的羞辱和压迫。强奸与战争的固有属性不谋而合,只是战争暴力的一种表现形式。男性对女性的性侵被克罗地亚女权主义者维斯纳·凯西奇视为“种族灭绝强奸,是男性毁灭其他男性乃至整个社会的荣誉,但与性欲无关”。美国历史学家玛丽·路易斯·罗伯茨(Mary Louise Roberts)在二战研究中指出,“性行为不是释放战争压力的副产品,而是权力的神话、象征和模式”。

历史上很多传统战争的冲突主体都发生在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民族群体在战争强奸的政治含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性别史家分析过女性身份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认为强奸的权力结构与国家政治的入侵有同构关系。“女性的身体被迫成为战场的一部分,成为国家权力斗争的领域。征服被占领国家的女性身体和征服领土具有同样的政治意义。”Djurdja Swick在《情感民族主义》中指出“强奸是一种羞辱和污染国家的策略,国家是女人的身体,或者说是女人”。
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叙事都不约而同地将女性、生育、维系家庭的角色纳入动员和宣传国家的意义中,通过“祖国母亲”的意图强化国家政治的规范,以此来鼓舞士气、振奋精神、召唤认同。这是一种有效的战争动员宣传策略。但这样的性别隐喻对应的是现实中的战争悲剧。正是这种民族主义叙事、女性的象征意义和战争中的性别化修辞构成了现实生活中强奸的文化基础——化身为大地母亲的女性符号使得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不可避免地成为领土入侵者的目标。Kneezer Swick说:“侵犯国家主权或自主权似乎等同于强奸妇女和占领土地。换句话说, 入侵者强行进入‘他者’的领地,可以理解为‘阴茎’的霸权行为。"
强奸导致的*和分娩也成为“人口清洗”的残酷手段。学者陈顺新也强调了性别话语中的“纯洁”与地缘政治中的领土“完整”之间的隐喻。由于强奸与打破贞操、性与生育之间的隐喻和关联,性侵在民族主义的叙事中充当了一种工具:对女性身体的侵犯打破了一个民族/种族的“纯洁”,并由此构成了对人口的变相清洗和对种族纯洁的所谓挑战和玷污。强迫当地妇女*、集体强奸或在家人面前强奸,意味着入侵者“渗透”了“他者”的领地,侮辱了其他人。历史上,由于性别和种族主义的双重叙事,在战争中被外国人强奸的女性也被自己的家人所排斥, 性羞辱变成了国耻。强迫被强奸的妇女生下孩子,在父权制和民族主义的双重战争逻辑下,侵略者对某个族群的妇女进行了侮辱和侵犯,被赋予了一个强势族群对另一个弱势族群进行侵犯的意义,这也构成了对这个族群的侮辱和伤害。
战争中的性犯罪不是极端条件下民族主义心理驱动的“即兴激情犯罪”,而是国家机构有组织、常规、有序进行的制度性性犯罪,“军人通奸”是国家父权制的引导和鼓励。就像慰安妇制度和军队妓院是有组织的,是政府授意的大规模侵害妇女行为一样,来自不同国家的慰安妇也分为三六类,服务于不同军衔的军官。对军事“性”的管理,其实与当局想如何控制入侵,让后者屈辱而顺从密切相关。通过实施性暴力,战争中的强奸是为了公布民族之间的力量差距,形成等级关系,从而达到侵略的目的。
面对战争、地缘政治冲突和国际争端,国家、民族、文化谱系和公民身份分别与性别交织在一起,产生了战争中的“强奸”现象。战争强奸的发生甚至可以分阵营,可见父权制的残酷并不是战争的秘密。据研究,当战争发生时,酒精的消费量会增加,崇尚武力和暴力的气氛浓厚,武器泛滥,社会失序。女性不仅受到战争的威胁,还面临更高的家庭暴力风险,更不用说跨国或跨种族婚姻中的身份问题了。对于不同的国家和阵营来说,战争的胜负和正义与邪恶可以白纸黑字的说清楚,但是对于女人来说,战争只有恶魔的面目。女人在战争中没有胜败, 而人类的战争史,就是女人的血泪史。
战争失语症:女性不仅仅是战争的受害者。
基于性别的战争话语造就了“英雄男人和被动女人”的二元对立。这两个战争性玩偶形象掩盖了女性在战争中的真实角色。在性别与战争的“刻板印象”想象中:男强女弱。男人好战、凶残、好斗;女人天生平和,抚慰人心。男人是外在的保护者,女人是内在的被保护对象。男人获得了英雄的桂冠和称号,女人却没有发言权。在战争的记录中,女性成了衬托男性英雄主义的下脚料,成了描述战争残酷性的牺牲品。
诚然,我们不得不承认战争给女性带来了无尽的伤害,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在政治冲突和战争面前没有主动权。虽然女性表现出更多的和平主义倾向,但并不是每个女性都是“和平主义者”。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军队中有雅典和斯巴达的女兵。两次世界大战也有很多女兵。中国花木兰为父从军的故事,展现了女性如何在“家庭-国家-民族”的战争叙事中突破性别局限,在战争中以不同维度积极行动。纵观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民族独立运动或反殖民主义的历史上,都有大量的数据表明,女性是国家动员的重要资源和力量。女人是战士,支持前线,投资建设, 并且可以和男人并肩作战。《我是女兵,我是女人》的书皮。
《我是女兵,我是女人》的书皮。

说到战争和女人,谁也不能忽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S.A. alexeyevich)。她的非虚构作品《我是一个女兵,一个女人》(直译为《战争的非女性面孔》)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苏联女性。她们是战争中的女兵,担任坦克手、枪手、后勤人员等等。阿列克谢耶维奇无意将女兵刻画成女英雄,而是以忠实的态度,以独特的方式展现了女性是如何被迫成为*手的。她们是因为战争失去孩子的母亲,是习惯搬运尸体的体力劳动者,是在战争中依然示弱温情的卫生指导员,是依然渴望穿上辫子和裙子回归正常生活的女性。
然而,军事和社会环境中的性别歧视进一步压制了在战争前线做出贡献的女性,消解了女性在战争中存在的意义。根据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记载,女性被迫参加战斗,却遭受恶意的性猜疑。她们被称为“战地妻子”和“战地妻子”,她们认为自己在战场上只能充当发泄*的工具,无论是来自敌人还是英雄。认为女兵能活着回来是因为她开小差或者出卖了身体,所以很难被战后的环境和社会所接受。即使战争结束,战争的阴影还是会萦绕在她们心头,女兵们只能通过沉默和隐蔽来抹去战争的影响。

此外,在越南战争期间,一位名为Dang Thuy Tram的军医在1966年至1970年间写了两本日记,记录她的战时经历。除了描述越南周围的乡村和人们,她还写了爱和失去,她的雄心和挫折,以及她努力理解战争对越南生活不断变化的影响。这部作品后来被女性主义地缘政治和情感地理学者视为战争中的典型女性案例——因为在战争中照顾家庭,她是越南的“道德母亲”;因为军医的职业,她也是“公民兵”。《Thuy的日记》中亲密而感性的描写与宏大而美化、阳刚而抽象的军事暴力形成了女性视角的逆向叙事。
女性口述的“小历史”向我们揭示了女性被压抑的战争经历。在国际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大舞台上,虽然仍然认为男性主导与武器、战争、外交活动和高级政治有关的活动,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已经开始打破这种偏见。女权主义国际关系学者辛西娅·恩洛(Cynthia Enloe)写道:“政府之间的关系不仅取决于资本和武器,还取决于作为符号、消费者、工人和情感安慰者的女性的控制。”她从女性在农业旅游、民族主义、军事基地和外交方面的生活经历入手,分析了国际关系的运作如何依赖于女性的努力和贡献, 同时在文化和制度上将女性排除在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权力中心之外。男性化的国际关系和政治决策中性别化的操作模式,使得女性不可能成为决定世界事务的真正决策者——女性始终处于政治权力操作序列的后面。
战争的背后,总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等不同的危机。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妇女不得不同时与种族掠夺、殖民侵略和性别不平等作斗争。在战争中,不仅妇女陷入贫困和困境,而且家庭破碎。同时还要求妇女支援前线,清理废墟,提供医疗救助,保证物资供应,支援社会生产。事实上,战争需要女性,而且往往迫使女性经历更严重的劳动剥削——家务劳动不再局限于为家庭服务,而是被提升为“国家的使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工人阶级地区的妇女被要求以低于男性的工资从事工业和运输,因此同工同酬和劳工斗争成为战争期间妇女斗争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美国家庭主妇填补了男性参战留下的空缺,涌向工厂和工作场所,也迎来了新的社会变革。当社会结构松散解体,性别问题高度军事化和政治化,女性的生存权和社会地位将面临新的冲击。
最后,有必要指出,更多的妇女参与战争以阻止战争。从一战二战的历史到现在离我们更近的地方,在对女性战斗人员的采访和记录中,有很多女性为了自己的尊严、人身安全、自己热爱的生活和下一代而战。妇女常常被迫参战,希望结束战争,妇女也常常为和平而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