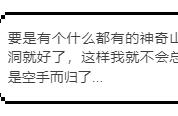2005年退休搬家到北京后,小区在朝阳路和通惠河之间。没事瞎遛达,才知道南北都是元明清三朝大运河漕运从通州进入北京城的重要通道和节点,沿途有不少历史遗迹和故事,逐渐有了些更多了解的*。 八里桥竣工于明英宗朱祁镇的正统十一年(公元 1446年),当时定名为“永通桥”,后因距通县 8里,俗称八里桥或八里庄桥。 八里桥是大运河通州漕运码头到朝阳门内皇家粮仓的陆路运输通道,桥下的通惠河则是漕粮过驳为小船后,逐级过闸运往东便门大通桥的水路通道。因为通惠河的水源不足,这两种运粮通道缺一不可。
八里桥南端东侧,有一座清雍正七年(1729年)的 “御制通州石道碑”。因土路大车在雨雪天无法行走,他花 343484两白银将土路改成石道。到了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又重修石道,全长三十多华里,路宽二丈,两旁土路各宽一丈五尺,用银 284900余两。并于四年后在二外北门朝阳路的定福庄路边立了座乾隆御制的 “重修朝阳门石道碑”。
除了元明清漕运重要节点外,八里桥还是 1860年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最后一役的战场。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大沽口炮台后进犯北京,僧格林沁统率蒙古马队七千、步兵万余名,从天津撤防退至通州、八里桥一带,与英法联军进行决战。尽管清军士兵表现英勇,但终因战法、装备严重落后而惨败。 八里桥之战,三万多清军伤亡过半,而一万人的英法联军只有十二人阵亡。 法军军官吉拉尔在《法兰西和中国》中对清军的英勇作战做了详细的描述:“光荣应该属于这些好斗之士,确实应该属于他们!没有害怕,也不出怨言,他们甘愿为了大家的安全而慷慨地洒下自己的鲜血。这种牺牲精神在所有的民族那里都被看作为伟大的、尊贵的和杰出的。… 这样的英雄主义在中国军队里是经常可以看到的;而在欧洲则以误传误,竟认为中国军队是缺乏勇气的,此乃是一大谬误。”
照片是通州八里桥南侧桥头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

1980年,香港李翰祥执导了《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形象地叙述了清咸丰末年的那段屈辱的历史。 2010年,在圆明园大水法遗址附近树起了法国雕塑家娜什拉-凯努女士制作的法国大文豪雨果的半身青铜塑像。
在雨果雕像南侧,一块书形石雕上,特地镌刻了雨果 150年前谴责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暴行的《致巴特勒上尉的信》节选部分。 “… 一天,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园,一个抢掠,一个放火。可以说,胜利是偷盗者的胜利,两个胜利者一起彻底毁灭了圆明园。” “…我们欧洲人认为是文明人,而在我们眼里,中国人是野蛮人,可这就是文明人对野蛮人的所作所为。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分别叫做法兰西和英格兰。但我要抗议,而且我感谢你给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统治者犯的罪并不是被统治者的错,政府有时会成为强盗,但人民永远也不会。法兰西帝国将一半战利品装入了自己的腰包,而且现在还俨然以主人自居,炫耀从圆明园抢来的精美绝伦的古董。我希望有一天,法兰西能够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将这不义之财归还给被抢掠的中国。”

2015年我与老伴去圆明园看菊展,也特地去凭吊了西洋楼各处遗址,拍下了雨果的铜像。

这张照片是在通惠河上游,八里桥西侧的雁翅护坡上拍的。
《通州志》中记载了明正统年间,祭酒李时勉所作的《永通桥记》:“通州城西八里河,京都诸水汇流而东。河虽不广,每夏秋之交雨水泛滥,常架木为桥,比舟为梁,数易辄坏。内官监太监李德以闻于上,欲与其地建石桥,乃命司礼监太监王振往经度之。总督漕运都督武兴发漕卒,都指挥佥事陈信领之,工部尚书王卺会计经费,侍郎王永和提督之,又命内官监太监阮安总理之。桥东西五十丈,为水道三券,券与平底石皆交互通贯,锢以铁,分水石护以铁柱,当其冲,桥南北二百尺,两旁皆以石为栏。表二坊,题曰永通桥,盖上所赐名也。又立庙以祀河神。经始在正统十一年八月,告成于十二月,明年三月立石。”
1860年英法联军的炮火炸毁了八里桥的石拦板和牌坊,1900年的八国联军又在八里桥附近与义和团发生了激战。雍正的御碑亭和通州运河码头验粮的大光楼都被侵略者焚毁。

八里桥东侧通惠河下游的照片。 我曾几次到八里桥流连,八里桥两侧南北雁翅护坡水边共有四只伏卧的镇水神兽 “蚣蝮”,造形极其生动。桥东侧两岸的石砌护坡很徒,老胳膊老腿的,我没敢下去。桥西侧两岸的蚣蝮我都下到水边,从近处仔细地观赏了它们。

1938年,日寇为修筑京通汽车路,将八里桥两端的路面垫高,降低了拱曲。 80年代,为保护古桥的历史风貌,减少洪水对桥的冲击,在桥南北两端开道引河,各建三洞水泥桥一座,用来泄洪分流,桥间以水泥构成分水泊岸。说实话这次保护使 576年历史的八里桥与两侧的现代水泥桥连在一起,视觉效果绝对不好!恐怕也是不得以而为之吧。 老八里桥经几十年汽车的辗压,伤害较重,大约 2018年在上游一百多米处盖起了单拱的新八里桥,通车后老八里桥禁行机动车,不久老桥就封闭维修了。
新闻本说 2019年底可完工,恐怕因新冠疫情进度受到了影响。至今 2003年了,我遛到那里好几次,两端还是围栏铁门关闭,奇怪的是工地上都没有施工的人影和动静,想问问看守的人员也见不到。

这是八里桥西侧南岸水边的蚣蝮,还是未封闭前去用手机拍的。桥两侧的蚣蝮都是尾部朝桥,头部冲桥外侧。
相传很久很久以前蚣蝮的祖先因为触犯天条,被贬下凡,被压在巨大沉重的龟壳下看守运河 1000年。千年后,蚣蝮的祖先终于获得自由,脱离了龟壳。人们为了纪念、表彰其家族护河有功,按其的模样雕成石像放在河边的石礅上,并说这样就能镇住河水,防止洪水侵袭。 其实 “龙生九子”的传说,直到明代弘治年间,才开始出现文字的记载。九子的名称和它们所持掌的功能也是五花八门众说不一,它们的形象更是凭空创造了,只不过随着皇家和官府的应用逐渐趋于一致。作为镇水神兽,“蚣蝮”的名称是现代《大百科全书》的说法。民间由于接受的来源不同,网上文章叫它什么名字的都有,如趴蝮,霸下,螭龙,避水兽…。
既是龙子,这只蚣蝮的头面部必然要像龙,头顶有一对犄角和飘扬的长髯。身体、四条腿和尾巴上都有龙鳞,四肢的肩腋部还有流云状的装饰图案。显然形象创作的意图在于强调表现它与神龙的血缘关虑。它的躯体和四肢非常强壮有力,但远没有龙蛇那么修长,反倒呈现了狮虎类动物的形状特征,艺人应是理所当然地部分吸取了石狮雕刻的表现手法。我国大约在东汉时就出现了石狮,宫廷和民间匠人的创作与工艺也日臻成熟完善,数量极多,还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流派。

桥西侧北岸的这只蚣蝮,右前肢掌下居然护着一只幼兽。自然而然联想起石狮的雌雄辨认,雌狮爪下通常是只嘻闹的幼狮,雄狮爪下一般是绣球(当然据说还有摆放左右位置不同的说法)。这种表现方法更似乎在说明,雕刻蚣蝮的石匠,是吸取了更早更成熟的石狮雕刻的表现手法。
这只雌兽的肘部和鬓角处还有漩涡状的卷发。不是女人爱化妆,上一图中的雄兽左颊也有三个卷发团。这是因为蚣蝮扭头注视水面的体位,脸颊与躯体紧贴,没有空间刻划表现了。 通常石狮的球状卷发毛团,布滿头部,雌雄都一样打扮,有人说古代官员家宅前石狮的卷发毛髻数量是有等级的,一品官员才准有 13个,所谓“十三太保”。故宫中的就任性了,有人数过说有四十多团。 还有南岸雄兽肘部的漩涡图案也不明显,恐怕也主要是角度和石材的风化损伤有关。

拍个细节。感觉石匠在创作中也蕴涵了很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性伦理,估计他小时必定也熟读过“人之初,性本善…”。
守河镇水是神话中蚣蝮的专职任务,上千年来卧在河边,瞪大双眼日夜专注水面,一分一秒未曾分神。有了幼仔自然也要 “子承父业”,从小就开始训练孩子的技能和职业素养。 右爪护住幼兽,主要是防止孩子不慎落水,在扑岸的惊涛骇浪中,可以给幼兽提供信心和安全感,同时又为它指示和纠正肢体的站位及目光的方向。
这座明代不知名石匠的 “蚣蝮母子”,可以认为是一座极其精美的雕塑艺术品。在我的眼光中他的艺术价值,感觉要远远超过近现代许多雕塑大师的所谓经典作品。比如荆州的那座高达近 60米的巨型关公像,花费五年建造,却又因“未经规划许可”,系“违法建设”而拆掉了,连建带拆的巨额资金也不知由谁来买单。

八里桥的桥栏望柱上有 31对精美的石狮,英法联军炸坏后也曾重新修复,解放后又对风化破损严重的一些构件进行了维修更换。
两侧桥栏末端各有一座蹲坐的神兽,北岸的两只头顶只有一支独角,南岸的两只却都是双角,不知是否性别标志?也有可能是过去风水学说中有关方位的规则要求。
这四只神兽也是龙首兽身长髯,肢体都有龙鳞,据说也是龙生九子之一。有不同的说法,有人叫作 “螭吻,霸下,朝天吼,戗兽”,还有人说是麒麟。 感觉它并未表达镇水的功能,视线更加关注于桥面上通过的行人和车马。古代石拱桥两侧的栏板有向下倾斜的重力存在,两端树立这种神兽的目的,似乎主要是为了抵消石栏板倾斜的重力趋势,使建筑结构更加牢固。

网上看到新闻,说 2000年在整修北京中轴线上的 “万宁桥”时,挖掘出了六只元/明时期的镇水神兽。我较懒,2018年10月才去一睹尊容,主要想去看看神兽的形象与八里桥蚣蝮是否一样?
元代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所建的万宁桥(亦称后门桥、海子桥…),在北京中轴线上的鼓楼和地安门之间。万宁桥下是元代通惠河上游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郭守敬主持规划开凿整修京杭大运河漕运的北起点。元代桥西侧建有控制水位的“澄清上闸”,过了闸就是什刹海积水潭,也就是元代大运河漕运的终点码头了。前海东岸路旁,一块巨大的泰山石卧碑上刻着描金的“京杭运河积水潭港”。
古代漕运除了粮食,还有大量各种商品的流动交易,也极大促进沿河各城市的经济繁荣,什刹海的“烟袋斜街”就在这桥附近。

解放后万宁桥桥面铺设了沥青,后来这段河道也改为暗河,填土建房。桥身下半部分被掩埋在路基之下,地面仅存桥两侧的栏板,文革前后我来北京也曾路过这里。
照片是桥南西侧树立的景点介绍,南岸西侧桥头有一座 1984年公布的 “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石碑。桥北头西侧有座 “澄清上闸遗址”的介绍石碑,还有个刻着 “中国大运河遗产区界桩”的三角石桩。

万宁桥东北侧燕翅墙上的一尊石雕像。经长年风雨剥蚀早已不堪入目,估计当年石料的材质也选择不当。兽身不辨花纹,兽首面目模糊,只能分辨出蚣蝮的首尾和四肢身躯。据说,这只蚣蝮的颌下镌有 “至元四年九月”字样,是元代遗物。 桥东河道中水极浅,前面有荷花残枝败叶,蚣蝮颌下我也辨认不出字来。

南岸的蚣蝮外形与八里桥的相近,肢体之间的肩腋部也装饰着 “行云流水”的图案,当然那叫“祥云”。古代画作中龙的形象都少不了祥云和海水的烘托,在北海的九龙壁和故宫的丹陛石中也都有这样的渲染,主要表现神龙在上天入海时动作的矫健和速度吧?现在 “行云流水”这个词,主要用在表现写文章和书法绘画过程中了。 有专家认为这只蚣蝮是明代补刻的作品,可见元朝的那只原物也就不到二百年就残不忍睹了,不得已明代时又按原样重刻了一只顶替上岗了。
这只蚣蝮躯体上的龙鳞,也不如八里桥的那么细致顺眼,鳞片显得很大。不知石匠是否敷衍了事省力气,还是官府要求的工期太紧张了?臀部鳞片的排列和覆盖连接顺序也与脊背处的排列不一致,显然极不合理。入水游起泳来龙鳞处是要戗水的呀!

专家认为桥西侧两岸的一对蚣蝮也是明代重新雕刻的作品。但它们与桥东侧的两只在形象上却有很明显的差别。它们的身躯更显修长,脊部突出,两肋处狭窄,龙首的吻部也较扁长。它们的尾巴更粗大,与靠河的前后肢一起垂向水面。我感觉它们有点类似鳄鱼的外形特征。但鳄鱼在古代似乎并不是个令人尊崇的善类,聘请它们镇河怕也不太可靠吧!
唐代韩愈被贬潮州刺史时,当地有很多鳄鱼,民众饱受其害。他于是写了一篇《祭鳄鱼文》,推心置腹地劝说鳄鱼改恶从善:“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归,以生以食,鳄鱼朝发而夕至也。今与鳄鱼约,差别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听从其言也。” 结果鳄鱼很快响应,迁徙六十里而去。《晋书·周处传》和《世语新说》中,还有个 “除三害”的故事,其中一害便是 “长桥下蛟”。其实这个“蛟”,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龙,或说是指 “鼍”、鳄一类的动物。有的传说是“兴风作浪、能发洪水”的龙,有的却说它是善变化、能兴云雨、利万物的神异动物。
万宁桥西南侧的这只蚣蝮的左前肢已经损坏,其实石材的质量看起来很好,原有的刀工刻痕很清晰,几乎没有风化现象。估计是人为造成的伤害,躯体上也有断裂的伤痕。

当时为皇城修桥的石匠,是不可能自作主张去刻画 “镇河神兽”形像的,肯定得通过皇上或权臣来拍板决定。万宁桥的三只完整的蚣蝮也没有确定是明朝哪个年号重建的,估计不会是在同一位皇上当朝的年代里,也不会是由同一位石匠刻的。否则万宁桥两侧对应 “龙子”的长像居然不一样,也太说不过去了! 明朝的皇帝也有几个表现很奇葩,不务正业。有的整天沉缅于炼丹吃药,有的醉心于钻研木匠手艺,朝廷大事任由佞臣权相瞎折腾。也说不定万宁桥的两对蚣蝮形象,就是不同权相根据自己的喜好和认知擅自确定的,谁也说服不了谁,结果就刻成了两对长相差异较大的龙子。皇上当然也没闲心去视察,结果就这样摆在桥两旁,令人无法理解地丢人现眼了好几百年。
中国古代尤其皇家建筑布局的基本准则之一,就是严格要求 “中轴对称”,以此体现天地阴阳的合谐统一,长幼贵贱的人伦秩序,以此表现壮严,平衡和稳定之美。昌平明十三陵前 “神道”两侧的几十对石兽,石人雕像就很完美地表现了这种理念。 可是京城中轴线上,鼓楼和地安门之间的万宁桥四只蚣蝮形象差异,却实在是绝无仅有的离经叛道,令人无法理解了!这其中一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故事,不过目前尚未听到有文史专家对这一现象的探讨研究和解读。 另外,元代北京城内的鼓楼并不在现今的位置,而是在今天中轴线西侧的 “旧鼓楼大街” 上,史载元明清三代都有雷击大火重建的过程。可以想象今天定义的 “北京中轴线”,在这三个朝代时有个逐渐完善和更加准确的过程。

这是隔河拍摄的桥西侧北岸的蚣蝮,尾巴和前后肢垂向水面,爪下还有一球状物体,想不出是什么,有人说这是它爪下的 “吸盘”。卧伏在水边的蚣蝮目光紧紧盯着石壁上水面处的一个球状物,有人说那是水位的标志物,叫 “龙珠”。 不论蚣蝮的形象有多少差异,它们的目光和专注的神态,都完美地体现出镇河神兽的职业素质。
再仔细看了这张照片,又产生一个不解之谜:这只蚣蝮的躯体与他身下的条石,是在完整一体的大石块上凿刻出来的吗? 可是它下垂的前肢下方,却明显有一条垂直的石缝。这又象是先砌好大条石岸墙,再将单独刻好的蚣蝮定位安装上去的。这样的施工工艺也不是不可能,众多皇陵中巨大的 “王八驮石碑” ,都是由碑首,碑身和龙子赑屃三部分通过榫卯结构组装成一体的,也能作到严丝合缝,不搖不晃的效果。但对这座蚣蝮形象而言难度太大了!它的躯体与身下的条石有太多复杂的接触面积,水平面和垂直面都有,前后肢和尾巴又相对较薄弱,很容易在凿刻和移位,安装过程中就不慎断裂的。 当然这条垂直的石缝,也可能仅仅是故意刻出的一条浅槽,其实蚣蝮和身下的石条还是一块整料刻成的。刻这条浅槽的目的仅是为了岸墙砌石的美观,故意营造成一种上下砖缝交错的视觉效果。
前几天,才从网上看到了 “远北地带”发表于2022年11月的一篇文章。他曾听说万宁桥西侧两岸石壁的水面以下还分别藏着一只昂首向上的蚣蝮,它们与岸上的蚣蝮上下对应,目光都盯着水面处的 “龙珠”,形成 “二龙戏珠”的造型。为此这位老兄还亲自穿戴装备,潜入水下寻找,并用相机拍下了照片。从他发出的照片看,似乎能分辨出龙珠下方确实各有一只昂首的龙头状的石雕作品镶在水下的石壁上,但看不出蚣蝮的躯体和四肢,水下光线和水草波浪等环境也影响了照片的清晰度。不论怎样 “远北地带”老兄的探索求实的精神,实在是令人由衷敬佩的!

绕过什刹海湖边新建的 “金锭桥”,到对岸去细看桥西北岸的蚣蝮。蚣蝮身后不远就是 “敕建火德真君庙”了,这座火神庙始建于唐贞观六年(632年),元代至正六年(1346年)、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都有重修。
蚣蝮虽有铁栅栏的防护,好在间隙较宽,并不影响象上一张照片中的红衣先生那样,伸进手机去拍照。 今年四月与老伴去爬鼓楼,又去看了万宁桥,蚣蝮的牢笼已被拆除了。看起来舒服了多,这当然也与观众素质的提高和文物管理措施的加强相关。

从这张照片看,蚣蝮左前肢处腹下的条石并没有横向的缝隙,说明蚣蝮与身下的条石原本就是一块整体的石料!可见技术高超的石匠艺人居然有心思象魔术师表演一下,通过 “偷天换日”的手法,使自己的作品给官家和百姓后人留下鬼斧神工的悬念和深刻的印象,也是为了营造一种广告效应吧。
条石的外侧还刻有燕尾槽,本来外侧相邻一块石料对应的位置也应有燕尾槽,安装时应镶进 “元宝铁”,使周边的石块都能紧固地相互勾连成为一体。从明清到现今,肯定也有过几次维修,现存的这些燕尾槽已经不完全对应配位了。
这只蚣蝮一眼看出这也是只雌兽,她的前爪下也有一只幼小的神兽。再凑近细瞧,小神兽的脸面居然是朝向岸内的,屁股冲向河水。这小兽蹲坐的朝向与八里桥下的小神兽完全相反! 很快心有灵犀,领会了这位明代石匠的创作意图,这只幼兽比八里桥下小蚣蝮的体形要小的多,岁数当然更小,似乎还没滿月在哺乳期。不休产假带着婴儿坚守岗位,这位母亲的职业道德确实难能可贵! 人家八里桥的孩子该上幼儿园了,自然要进行 “早教”,不输起跑线地学习知识,提高本领。咱家孩子刚出生半个多月,让拍岸激浪和震天波涛吓着了可不是小事! 隔着时空,与几百年前的石匠神会沟通,探讨作品创作理念,也是一件十分有幸有趣的事情!
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是徒弟在制作石料毛坯过程中,计划不慎雌兽爪下位置预留的体积凿得小了一些。听过有“长木匠短铁匠,不长不短是石匠”这样的说法,石匠下料当然是个很重要很精准的环节。比如古代石桥拱券上方圆弧处的石料,先要根据设计的半径和使用的数量,还要算出楔状石块上下沿尺寸差距,不同位置的石料恐怕还不完全一样,这样才能使拱券美观并保证桥梁的结构承重强度。尺寸不准确,恐怕过辆重载大车就会将石桥拱券给压塌了。 假定真是徒弟下料的毛病,事已至此,经验老道的师傅也只好 “因料用工,顺势而为”了。迫不得已之下,却创造出了更加意味隽永的完美艺术品。在玉石等贵重材质的雕刻艺术创作中,这种因料用工的功力更是极其重要的。即使你的成品再精美,制作时却剔除了大量无法再利用的垃圾碎屑,可以想象东家会付给你多少工钱!
另一方面,众多同一种类雕塑作品的形态完全严格统一,制作再精致也算不上是好作品。我看过一些不同的石狮,有宫廷的,有民间的,有南狮有北狮,有的壮重威武,有的灵动活泼。我还曾专程去卢沟桥数过狮子。雌狮爪下的幼狮大都是神态各异的,有的安静依偎,有的甚至四脚朝天地嬉闹。幼狮的位置和体形大小也不是绝对一致的,石匠随意发挥,表現的余地很大。

万宁桥西南侧手机拍摄的桥体,桥梁西侧的栏板和望柱。有的是古代原物,风化剥蚀较严重,还有的经过不同年代维修。南北两端的栏板显然是崭新的仿制品,估计是最近替换了无法修复的部分构件。
有人说桥洞下的墙壁上刻着 “北京”二字,水面漫过这二字,意味着将要发生洪灾,我老眼昏花也没看见字迹。东西二侧桥洞的拱券上方正中,各有一石雕龙首,目光向下盯着水面,风化也较严重,照片中也被垂柳枝叶遮住了。有人说他俩也是镇水的蚣蝮,连同岸边伏卧的四只,万宁桥共有六只蚣蝮。

桥西南北侧是澄清上闸的 “绞关石”,只留下一块斜立在岸边,其它三块都已断毁,根部的断痕还埋在那里。它们本是两块一组斜嵌在两岸边,上端都刻有圆孔,插着木轴是升降木闸门时的吊索转折点。古代两岸的闸夫相对排开,象组队拔河比赛一样,同时用力提升或关闭木闸门。两块绞关石之间岸边垂直的石壁上刻着深槽,是闸门上下的轨道。

把八里桥和万宁桥两处西侧的蚣蝮照片组合在一起,公兽与公兽,母兽与母兽,这样可以更好地进行比较。
两处作品显然不是出自同一技术流派的匠人,几百年前明朝的两位不知姓名的石匠艺人,不知是否老乡?他们是否接受过某一门派技艺的传承和影响?更不知他们的生命周期有无重迭,是否有过会面交流和讨论?在创作同一种被尊崇的神兽作品时,对其形体,神态,以及寓意的表达 …,都有哪些异同和特点?
我觉得他们都是伟大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都应收入到博物馆中,大几百年来任其经受严寒酷暑风吹雨打,实在有点太可惜啦!

右图八里桥蚣蝮雄浑强壮的躯体和脊柱扭成了 S形的曲线,感觉上更接近狮虎这类哺乳动物。常见的猫狗体态,也很容易成为石匠观察和摹画的模特,他在雕刻创造中借用,自然有深刻的印象,体态的把握肯定要真实准确和生动的多,连脊椎骨的每亇关节都能细致表现。我家就养了个猫,每天逗它伺侯它,看到这只蚣蝮的形体姿式感觉也很眼熟,自然联想到自家猫主子倦卧着休息浅睡的样子。
古人对鳄鱼观察的机会应该也不多,万宁桥蚣蝮的脊柱呈 J形,像鱼一样在静态时比较生硬,是不会呈现优雅的 S形曲线的。
古代传说中的镇水神兽蚣蝮,到底是形似鳄鱼一类的卵生爬行动物,还是属于狮虎之类的哺乳纲食肉目动物?这永远是个谜。他们应该与自认为是 “真龙天子”的古代皇上同宗,它们的亲爹神龙本身就是古代神话传说中创作出来的动物。
小时见过一次家乡远处大河中的龙卷风现象,一条黑线卷上天际云中,有大人说那是 “龙吸水”。那时还听过白龙和黑龙的故事,记得一个角色名叫 “秃尾巴老李”,故事情节却记不清了。

传说蚣蝮是大运河专职的镇水神兽,我没机会作更多实地探访,从网络中收集了一些图片。
左上是通州张家湾村北,通惠河故道上土桥(广利桥)的蚣蝮。目前保护放置在土桥村新建的小区7、8号楼之间。 左中是 2013年6月16日,在山东元代临清闸雁翅与裹头的交汇处出土的镇水兽蚣蝮。长 1.1m,宽 0.46m,底座加兽身高 0.36m。 左下图是 2018年,聊城市阳谷县张秋镇的京杭大运河中,再次出土一尊水兽,蚣蝮口中还含着一条鱼。 据推测,该水兽系明朝或元朝文物。 右图是山东兖州城东,横跨泗河的金口坝,坝西端翼墙上部有精雕石质卧水兽 1对,体长 1米,雕刻精致,栩栩如生。
从八里桥万宁桥到运河沿岸多处的蚣蝮,我们可以看出,所有形象外形大体是一致的,但从审美角度看也有明显的差距。有的作工粗糙,形态呆板其至比例失调。
这可能与古代石匠技艺的传承有关,仅从蚣蝮的尾巴和前后肢是否垂向水面这个细节,就似乎可以想到这些石匠是师从于不同的祖师。 从审美效果差距,也可联想到古代石雕作品与某些专类作品的市场需求有关。相对而言市场需求石狮的数量最大,从官府衙门,寺庙园林到大户宅门都有需要。石匠队伍中自然也分化成了专业分工,肯定有部分石匠是专雕石狮,通常只会凿刻石磨碾子和建材的一般石匠,是干不了这种专业活的。不同专业的石匠通过家族和师徒间的技艺传承,越发熟练和创新,作品才能更受欢迎。
石刻蚣蝮作品的市场需求远比石狮要小,专业的工匠人数自然更少,技艺提高的速度和扩散的地域范围当然要小的多。万宁桥和八里桥的作品是京城的门面,朝廷有能力准确选择并高薪聘请大师级的专业工匠,而地方政府或民间显然没有这种选择条件和财力了。所以众多图例中蚣蝮艺术水平参差不齐,有的甚至感觉很丑陋。反观各地的众多石狮雕像,尽管也有水平差距,但基本形体统一,都能被不同阶层的用户所接受,远不象图中的蚣蝮雕像那样相去十万八千里。

以下的左上图是江苏泗县曹苗村崔庄运河边,东八里桥上的 “镇水神兽”。长约 1.2米,宽 50厘米,高约 60厘米,形体精美,遍布鳞片,仪态威慑,长方形底座浑然一体,毫无瑕疵。 左下图是在南京外城上坊门附近,运粮河上一座始建于明正统五年(1440年)的七孔石桥,曾被命名为“上坊桥”,百姓俗称“七桥瓮”。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神兽的分水尖被雕刻成 “人面分水兽”,四方脑袋象在作伏卧撑。 右上图是去年9月,在前门城楼东南角的正阳桥遗址考古时挖掘出的一只蚣蝮。该兽用花岗岩雕刻而成,俯卧在雁翅石条上,形态浑厚大气,造型逼真。头朝东南,俯向水面一侧;尾向西北,略弯曲,身被鳞甲,局部饰祥云纹,推测为明代遗存。距现状地表深 2.5米,长 3米,宽 1.4米,高 48厘米。 右下图是位于昌平县城南 10公里、跨北沙河(温榆河)水面的朝宗桥。是建于明正统十二年(1447)的七孔石桥,桥下的一只蚣蝮已经破损很严重了。
传说中蚣蝮是专门在大运河镇水的,别的大河流域古代有无蚣蝮雕像?我没考察过,也不敢肯定。反正在不同河流的古代石桥拱券上,也见过石刻的龙首造型,有的还支撑着前肢,眼晴也盯看桥下的流水。也有人说这个龙首就是镇水的蚣蝮,说的当然也有道理。

实际上古时代官府和民间用于镇水的神兽形象有多种。 1973年,在成都天府广场旁,挖出了一只古代修筑都江堰工程时雕凿的镇河石犀,李冰是公元前250年秦昭王时的蜀郡太守,当时共刻有五只石犀,安放在不同地方。唐朝大诗人杜甫还专门为此写了一首《石犀行》的诗。 1989年,山西永济县经过一年多的查访勘探,发现并出土的唐开元铁牛、铁人。他们铸于唐开元十三年(725年),为稳固黄河两岸渡口 “蒲津浮桥”,维系秦晋交通而铸。元末桥毁,久置不用,故习称 “镇河铁牛”。因黄河河道变迁西移二公里,逐渐为泥沙埋没。 沧州铁狮子,又被称作 “镇海吼”,铸造于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关于其来历有多种说法:一说是后周世宗柴荣北伐契丹时,为镇沧州城而铸造;另一说则认为铁狮位于沧州开元寺前,腹内有经文且背负莲花宝座,故应为文殊菩萨的坐骑;还有人根据铁狮的别名 “镇海吼”,推测是当地居民为镇海啸而建造的异兽。 还有颐和园昆明湖边,乾隆铸的精美铜牛,腹背还特地镌刻了篆体四言体的《金牛铭》:开头就是“夏禹治河,铁牛传颂,义重安澜,后人景从…。” 可见从远古夏禹那时起,就以铁牛形象专用作镇水的偶像了。

其实在古代民间尤其农村,百姓对旱涝洪水的恐惧最依靠的是“龙王爷”。有人说,我国古代各种寺庙中,民间的龙王庙数量最多,其次才算关帝庙。
照片是我们附近通惠河高碑店古闸的龙王庙。这座庙建于明嘉靖辛酉年(1561年),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重修。上世纪 60年代被毁,2011年重建。重建后的龙王庙为两进院落,山门殿三间,正殿五间有龙王爷等供奉的神像,东西两侧各有三间偏殿。我进去过一次,看见个象是道教的人,穿着长袍在给人算命。 沿河边遛弯时与老人聊天听说,河边好多村子早年间都有龙王庙,毕竟事关能否风调雨顺,都指望拜龙王爷再加上自己汗水摔八瓣,能有个好收成。
其实蚣蝮和它爹龙王爷,往往并起不到民众祈愿诉求的保障作用,反而后来出现了调侃的谚语 “大水冲了龙王庙”!

。